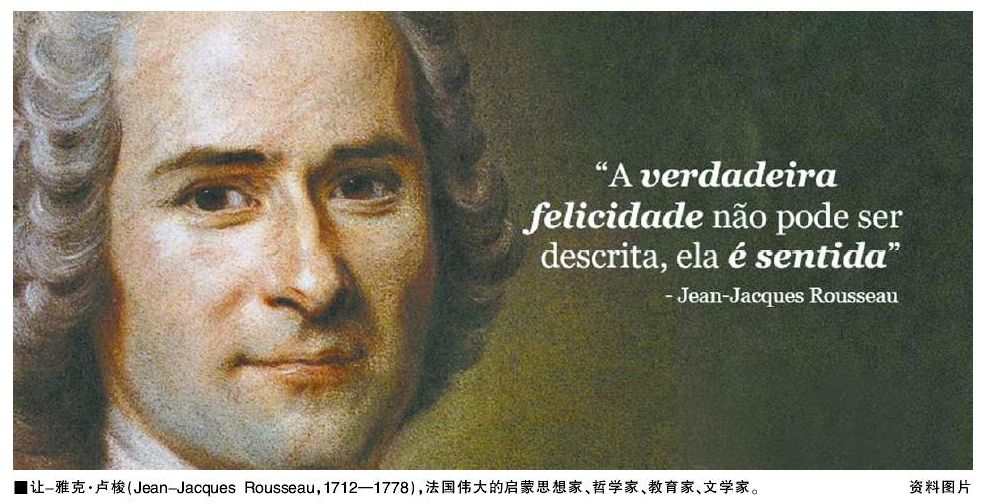
自伯克以来,一提到法国大革命,就自然而然地指向卢梭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卢梭的政治哲学虽充满了革命的教诲,但其本意并不教导革命。卢梭诉诸自然自由和道德自由,这在现实社会生活层面上是不可操作的,自由最终必然陷入孤独自然人的内省中,这才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最终旨归。因此,将卢梭的政治哲学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或值得商榷。
卢梭构建的道德共同体本身也是枷锁
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卢梭颠覆了古典政治哲学德性至上的最高目标,把德性仅仅当作实现自由的手段,从而奠定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自由至上的最高目标。卢梭关于自由的理解在于,人具有原初的自然自由和人之为人的尊严的道德自由。围绕这两个方面,他激烈地批判了充满着奴役和不平等的现代政治社会,并提供了两种匡正的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重返自然状态,寻找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根据。通过对自然状态的深入考察,卢梭发现,自然人依其本性是自足的。这种原初自由使自然人离群索居、悠然自得。但是,历史的偶然性和不可逆转性导致了自然状态成为遥远的过去,因此,复归自然自由和平等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正如苏联学者阿思穆斯所说的那样,“卢梭虽然迷恋既往,他却没有走得那么远。他在致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的信里解释道:‘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回到野蛮人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更幸福些”。自然自由是在自然意义上使用的自由概念,它的主词是与动物无异的自然人,只有作为自然的奴隶的自然人才拥有如此这般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然自由毫无意义,必然被具有社会性的现代人所摒弃。
第二种方案是诉诸以公意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据。当“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出于自存的考虑,人类只能依靠约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时,基于约定的共同体必须确保“每一个与全体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社会契约便造就了一个独立“人格”——道德共同体。作为立法者的每个人必须消融自己的特殊意志,意欲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意欲的普遍性的东西,并以此作为法律而固定下来;每个人必须服从他作为立法者制定的普遍性的法律。这就是卢梭通过公意原则对自由尊严的升华。公意即上述意欲普遍性东西的理性意志。卢梭认为,依自然本性的特殊意志只有向往普遍意志才能实现自身,才能实现道德自由。
但是,这一方案同样是行不通的。其一,道德共同体需要完全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用“道德的生命”代替“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这就使以公意原则为基础的道德自由与道德共同体空无内容,仅具有纯粹抽象的形式而已。其二,卢梭否认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既然历史的进程不包含必然性,因此,这样的道德共同体的实现只能依赖于不可知的机缘,而这无异于宣告了诉诸道德共同体这一方案的彻底失败。况且,即便道德共同体的构建是可能的,这一道德共同体也不会完全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平等。因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自己构建的道德共同体也是枷锁。
成为孤独的道德自然人
既然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自由,人只有从社会重新回归自然,才能找到自由。这就是卢梭提供的“最终选择”:退隐社会而成为孤独的漫步者。
卢梭的政治哲学中隐匿着“成为孤独的道德自然人”的伏笔。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卢梭将善和道德区分开来,道德总是与成为共同体中的人的努力相连,而善则不同,自然人依其天性就是善的。虽然卢梭怀揣着斯巴达政制的理想,但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他毫不犹豫地赞赏前者。因此,对卢梭而言,不仅基于自我保存的社会契约不是人类生存的原初事实,是派生的;而且自我保存这一自然人在为了生存的努力中体验到的生存情绪,因其带来自然人对人类活动的关切而导引了人类的悲惨境遇,也不是人类原初的生存体验,同样是派生的。卢梭极端地将人类一点点的努力都看作是自然善的障碍,进而看作是人类基本愉悦的障碍,那么,只有回归最基本的体验——自然善,人才能够快乐起来,否则就只能悲惨地过活。卢梭的这一感伤情怀注定了他只能成为生活在社会边缘而无法成为社会一员的孤独的人。
事实上,卢梭本人也确实放弃了对现代政治社会做任何的抵抗而选择了隐退。卢梭将探讨政治权利原理的《政治制度论》仅仅出版了其纲要部分——《社会契约论》,而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代之以写作《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孤独漫步者的遐思》等自传性题材的作品。尤其在《爱弥儿》中,卢梭将爱弥儿培养成了一个道德自然人。
此外,卢梭退隐社会而成为孤独的漫步者与他晚年不幸的生活遭遇也是分不开的。晚年的卢梭将自己比作“人群中最深情的人”,他为匡正现代政治社会的奴役和不平等所做的努力换回来的却是同代人的厌恶和唾弃。卢梭试图为自己辩解,但是“指望公众回心转意实在是个错误”,他最终“彻底放弃了在有生之年使公众回到自己一边的念头”,所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听天由命,不再一味与命运抗争了”。卢梭从社会中退隐,成了一个孤独的漫步者。
罗伯斯庇尔无比崇拜地称赞“卢梭是唯一以其灵魂的高尚和人品的伟大表现出自己是人类当之无愧的师表”,承诺“将永远忠于我在你的著作里汲取来的灵感”。卢梭本人并没有教导革命,是罗伯斯庇尔把《社会契约论》当作革命行动的法典。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