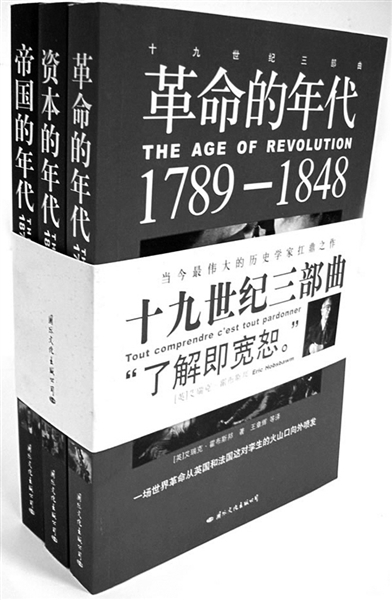
李·哈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若一个人寿终正寝,他年轻时的罪恶通常都会被原谅,即使身边有人记得这些往事。或者至少不会大肆宣扬也不会在冗长的讣告中提及这些罪恶。
但是,以95岁的高龄去世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却是这一规则的例外。就在霍布斯鲍姆去世的消息公布当天,英国著名学者威尔逊(A. N. Wilson)就令人惊讶地写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猛烈攻击这个常常被认为是当今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霍布斯鲍姆会很快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他的书将来不会有人阅读,虽然讣告中把它们说得天花乱坠,但这些比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品好不了多少,文笔糟糕透顶。”对一个备受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举动值得我们解释一下。
威尔逊是托里党人,换句话说是保守派,保守派不赞同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解读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但意识形态差异并不妨碍其他保守派历史学家在霍布斯鲍姆的棺材架边唱赞歌。绝对正宗的保守派人士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卫报》上的回忆文章中就称霍布斯鲍姆是好朋友。他说虽然霍布斯鲍姆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但仍然是“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仍然是“英语写成的现代世界历史的最佳入门书。”
两位杰出的保守派思想家为什么采取如此针锋相对的立场呢?笔者认为答案就在于一个简单的词:斯大林主义。
在威尔逊看来,霍布斯鲍姆首先是“原谅斯大林屠杀”的人。在文章中,威尔逊提出了非常有趣的问题,霍布斯鲍姆在1930年代在剑桥读书时,是不是像他的朋友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和盖·伯吉斯(Guy Burgess)一样是苏联间谍呢?如果是,霍布斯鲍姆就不仅是蹩脚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个叛国者。(别忘了威尔逊多才多艺,还是个小说家,而小说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霍布斯鲍姆的崇拜者当然会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他们心中的英雄怎么可能成为苏联间谍呢?但是他们无法否认霍布斯鲍姆在年轻时是被称为工人天堂的苏联的狂热支持者。不过,这个事实并不说明霍布斯鲍姆有多特别。在西方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许多好心的美国和英国知识分子都称赞过斯大林时代的俄国,在离开孤立的苏联后毫发无损。可是在三十年代的这些苏联同情者中间确实出现了一些感到幻灭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后来成为批判苏联最猛烈最深刻的批评家。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1931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最著名的书《中午的黑暗》仍然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当时只有15岁,生活在柏林的霍布斯鲍姆也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凯斯特勒是早期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例子,但他也不是孤立的。其他一些左派分子也抛弃了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因为1939年纳粹和苏联签订的臭名昭著的友好条约令他们感到绝望,该条约开辟了第三帝国和苏联征服和瓜分波兰的道路。当然,有很多共产主义者仍然忠诚于他们心中神圣的事业,其中就包括了霍布斯鲍姆。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不管是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还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的残酷镇压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足以让人有理由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之后,他才正式终结共产党员的身份,这也只是因为党员身份失效了。
确实,苏联解体几年后,霍布斯鲍姆出版了一本主要的著作《20世纪史:极端的年代1914-1991》,其中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苏联实验让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早该如此了。他的许多批评家肯定认为如果霍布斯鲍姆到此为止,他或许能够挽救自己的名声,不至于被指责为英国最长寿的斯大林主义辩护士,霍布斯鲍姆并没有到此为止。1994年在英国电视台与迈克尔·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的对话中,霍布斯鲍姆清楚表明,苏联实验的问题并不是它损失了千百万人的性命而是没有能创造出他梦中的乌托邦典范。如果实验成功,损失千百万人就有了正当性。毕竟,霍布斯鲍姆忸忸怩怩地说,我们不是都同意在二战中为战胜法西斯主义牺牲千百万人是值得的吗?
奇怪的是,这种令人震惊的观点被霍布斯鲍姆的崇拜者视为其最大优点。他的兴趣就是宏大历史叙事,即提供一种包含一切的全景式的历史事件的画面。在历史学家往往专注于对历史中的孤立片段的狭隘的详细的分析的时代,看到一个历史学家有足够的勇气把人类命运作为其研究的主题绝对感到新鲜有趣。毕竟,寻找主导性的框架,用来为看似破坏性的事件的令人吃惊的变幻无常赋予意义和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更可靠的遗产之一。但在这种宏大理论有一个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即它允许或者鼓励宏大叙事理论家们用目的来为那些最邪恶、最残忍的手段辩护,甚至包括屠杀千百万无辜者。
但是,如果宏大叙事理论家真诚地相信预期目的(end in view)能够终结全人类的痛苦和苦难,这种立场或许有些邪恶的道理。这是卡尔·马克思本人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从来没有怀疑历史是有目的的,即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在马克思看来,这将造成历史的终结,或更确切地说是历史噩梦的终结,血腥的战争和革命将永远消失。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在欧洲启蒙运动高潮时充满希望地预测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一旦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永久和平的时代就要到来。
对马克思和他的早期追随者来说,这样庄严和高尚的目的能够为众多的暴力和血腥活动辩护。但是假设允许他们瞥一眼未来,亲眼目睹打着马克思的幌子进行的巨大社会实验连同其无尽的暴力和血腥不仅没有带来任何进步而且造成大屠杀、灾难性的失败和毁灭,那时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显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霍布斯鲍姆被允许看到了马克思没有机会看到的未来,我们知道他的答案是“唉,要是成功了,。。。”
这个答案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崩溃之后,霍布斯鲍姆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历史终结的场景的新信徒的时刻放弃了历史终结的所有希望,这一点充满讽刺的味道。这些知识分子跟随弗朗西斯·福山的脚步重新运用马克思的宏大辩证法,相信历史的最后阶段已经逼近,不过高潮并非全球拥抱共产主义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支持下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胜利。
不用说,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历史终结论没有任何意义。他写到,福山是伏尔泰的《憨第德》/《老实人》(Candide)中的老学究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总在安慰学生他们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霍布斯鲍姆认为历史不可能很快到达高潮,在后9-11时代的我们已经领教过这个严重的教训。实际上,霍布斯鲍姆在晚年明确指出,他也不知道历史的下一步将把我们带往哪里。
可以被称为历史不可知论的这个立场在我们许多人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中有多少人知道当今世界会走向何方呢?但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霍布斯鲍姆心知肚明。笔者认为在苏联崩溃之后,霍布斯鲍姆仍然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主要是出于在对他充满幻想的青年时期的感情依恋,他有时候几乎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决不能放任年轻时的热情影响成年时期的判断。认识到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论是个幻觉后,霍布斯鲍姆本来应该公开忏悔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这不仅仅是说霍布斯鲍姆错了,严肃的思想家都可以被原谅,而是他在思想上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却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早在1994年,最深刻的批评家之一,聪明的美国历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就指出了这个致命的缺陷。此人在82岁时去世,只是比霍布斯鲍姆早走几天。让尤金·吉诺维斯的批判如此强有力的因素是像霍布斯鲍姆一样,吉诺维斯从前也是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但与霍布斯鲍姆的逃避不同,吉诺维斯有勇气接受历史的教训。实际上,吉诺维斯的思想诚实迫使他不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彻底放弃了进步主义,这个动作的最终实现是他不仅转向保守主义而且成为罗马天主教徒,这个事实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死亡没有引起自由派媒体对霍布斯鲍姆之死的源源不断的颂歌。
与威尔逊及弗格森这些永远的保守派不同,吉诺维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使他有能力抓住霍布斯鲍姆的后苏联思维中“内在的矛盾”。 吉诺维斯在1995年为《新共和》撰写的《极端的年代》书评中写到“霍布斯鲍姆从来没有提到经济理论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应用的先驱,本世纪前几十年的意大利社会思想家菲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根本没有求助于帕累托的‘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s)概念。”
吉诺维斯当然知道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最严重控告。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内,帕累托的名字总是被诅咒的对象,理由不难理解。如果帕累托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错误的。更笼统地说,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如果正确,将给所有希望历史终结以及任何形式的进步主义的人以致命的一击,无论是马克思的历史终结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帕累托以尽可能直言不讳的话语指出,历史是无休止的循环过程,其中一小群体即精英分子获得了对社会其他人的征服和控制。但是,位于顶端的精英群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新精英群体的挑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老精英失去了对权力的控制,通常不过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牢牢抓住权力的方式,他们的先辈非常清楚如何为自己及其后代攫取权力。这时新精英就会取而代之,而且常常清理旧精英,排除其他任何人自己当家。但是,这种循环注定要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根本不能指望历史的终结。
简而言之,帕累托不仅仅提出历史不可知论而且提出赤裸裸的历史悲观主义。变化肯定发生,但并非走向进步。有些时期或许比其他时期更好些,但即便如此,这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当然不是人类必然走向进步的证据。
正如吉诺维斯所说,如果霍布斯鲍姆在1994年成为帕累托的最亲密追随者,他就有勇气走出阁楼,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正如阿瑟凯斯特勒在半个世纪前所做的那样,并认识到人类必然进步的神话背后的愚蠢。任何一个真正的历史悲观主义者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将要求霍布斯鲍姆摆脱其青年时代的热情或者罪恶,那他就被给予比大部分凡人更多的时间改变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不用说,帕累托式的历史悲观主义并非人人都喜欢。但它确实能发挥巨大的补偿作用。用以显示人类必然到达承诺的理想国的宏大历史叙事一次次地被真正的信徒滥用,他们轻易地相信为了更快速地实现历史的终结而死掉数百万人不过是付出的微小代价而已。与历史必胜主义者不同,历史悲观主义者从来不会欺骗自己或欺骗别人相信今天杀掉数百万人是在为未来数十亿人的幸福做准备。悲观主义者抗拒乌托邦的诱惑,因而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改良的努力上,不是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为理想国而是让它比不做努力时稍微好一点而已。
长寿的霍布斯鲍姆的最重要遗产或许是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连最有智慧和最博学的人也都可能欺骗自己,竟然会相信荒谬透顶的观点,即最不可思议的滔天罪行不过是人们为实现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而付出的微小代价而已。
译自:Eric Hobsbawm, Eugene Genovese, and the End of History by Lee Harris The American October 5, 2012
